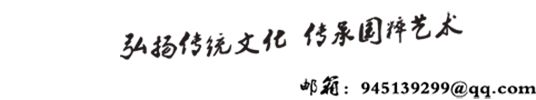墩的西北,沙丘逶迤相拥,像一群黄褐色的巨兽在深夜伏卧。沙丘之上,新栽的梭梭苗刚刚成活,怯怯地伸展着稚嫩的枝桠,为无尽的苍黄点上些微绿意,稀稀落落,如同天穹不慎抖落下的几粒星屑。沙坡之下,一弯清泉悄然静卧,形似新月,自南向北伸展。南北不过二百米,东西宽不足百米,水色澄澈,如沉璧,如凝脂。泉边芦芽与蒲秧密密匝匝地生长着,绿意盎然,簇拥着这小小的一泓水,恰似造物主对焦渴沙砾的一点垂怜。泉水无声地半抱着古老的平川墩,给它披上了一袭神秘而湿润的薄纱。在这干渴的天地间,水与土的相拥,温柔得几乎令人心颤。

也曾听闻乡野老者的揣测。也许是当年夯筑烽燧时,为取土而掘出的深坑,经年累月,竟蓄成了这一汪活水。然而细想烽燧的体量,实在耗费不了如此多的泥土。再看附近其他烽燧遗迹,其土质也并非就地掘取,平川墩自当不能例外。排除了这人力所为的可能,月牙泉的存在,便愈发显得不可思议,只好归于天地的玄机。大地血脉偶然在戈壁表层的一次显露,是亘古荒凉里最温柔而执拗的奇迹。那无声涌动的泉水,仿佛是时间本身在干涸的沙砾中潺潺流淌。
人间几度沧桑,世道几番变幻。四十年光阴,不过天地一瞬,却足以令昔日黄沙漫卷的戈壁,改换了容颜。当年风沙肆虐之地,如今已是千亩良田铺展。戈壁的边缘,梭梭树、沙枣树、红柳树,如绿色的卫士般葱郁成林,枝叶伸展,摩挲着高远的苍穹。三北防护林浩大的工程,如同在大地干渴的皮肤上精心绣下的绿色经纬,昔日风沙蔽日之处,竟也闻得见鸟语,嗅得到花香。极目远眺,戈壁的苍茫底色依然,大漠的浩瀚筋骨依旧横陈。荒原上有了新的笔触。巨大的风机叶片在长风中缓缓旋转,划开无形的气流。成片的光伏板阵列于骄阳之下,反射出耀眼而沉静的光芒,像无数面收集天光的银镜,这是人类在古老荒原上用科技手法刻下的最新印记。

我立于墩下,泉畔,看水中倒影。天穹澄澈,云朵悠游,风车巨大的影子与墩台古朴的轮廓在水中交织、荡漾。恍然间,仿佛看见时间本身在此显形,一层层叠加。月牙泉,这大漠之眼,它映照过秦汉的烽烟,唐宋的清风明月,流淌过明清戍卒的乡愁,如今,又平静地收纳了风机悠长的弧线与光伏板冷冽的辉光。它不言不语,只是以千年不变的澄澈,默默见证着沙海的退却、绿洲的蔓延、犁铧翻开新的泥土、现代的科技在古老的西风中悄然轮回转换。
清泉无声,亘古如斯。它滋润着岸边的寸寸生机,也以明镜般的心映照着平川墩的沧桑轮廓。泉与墩,仿佛一对被时光封存又时时苏醒的古老魂魄,在亘古的荒凉与蓬勃的新绿交替,在沉寂的历史与喧嚣的当今轮换,执拗地兀立着与时空默默相对。泉和墩的静默,胜过万语千言。墩和泉的存在,本身就是大地上最深沉的回响,惊醒着每一个红尘俗世的过客,纵使人间万象更迭,风沙与绿意的角力总不停止,总有一种绿意坚韧的温柔,自洪荒深处涌出,在时空无垠的戈壁滩上,汩汩流淌,映照出天空与人心深处,那轮生生不息的皎洁月光。(注:文稿图片由作者提供)
作者:张掖市临泽县 刘爱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