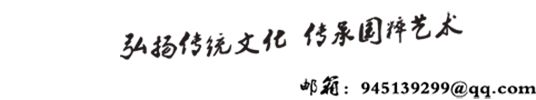后半夜的锁阳城是活的。我跟着王秀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,手电筒光束切开浓稠的黑暗,照见城墙上粟特商人留下的蹄印。这年五十五岁的文保员忽然蹲下,军绿色棉袄蹭过骆驼刺,发出细碎的破裂声。

“塌了半尺。”她抓起一把浮土任其流泻,沙粒撞击陶片的声音像在敲打编钟。三天前那场八级风撕开了时间裂口,露出汉代夯土层里蜷缩的黑色炭迹,残损的简牍上依稀可辨“元狩二年”字样。
我们跪在塌陷坑前记录坐标时,王秀兰的保温杯突然滚落。她慌忙捡起这个印着“2016年自治区文保先进工作者”字样的搪瓷杯,指腹抹过杯身裂纹:“父亲当年抢救文物用的军用水壶,现在还在工作站陈列柜里搁着。”
她讲述的1962年大沙暴带着铁锈味。那时她父亲还是公社拖拉机手,看见风沙掀开城南佛塔地宫,鎏金菩萨像的衣袂在沙尘里翻卷。全乡人举着马灯连夜转移文物,装粮食的麻袋裹住经卷,怀孕七月的母亲在牛车上用体温护着彩塑佛头。“后来那尊佛头现在在省博,三年前女儿带着学生用矿物颜料做分层补色,笔尖比父亲当年数的麦粒还细。”她说这话时,手电光正扫过残陶堆里半截可口可乐玻璃瓶,瓶底刻着“1987”。
凌晨三点十七分,我们停在西北角墩最高处。王秀兰忽然解开棉袄,从贴胸口袋掏出个油纸包。展开是张铅笔拓片,线条游动着晚唐供养人的裙裾。“父亲十年前临终前攥着的,”她将拓片覆在城墙新裂缝处,“他说这块砖该在今年现世。”
风突然转了方向。我听见某种呜咽声,像婴儿含混的呓语。王秀兰从残陶堆里抽出支细长物件——是半截汉代骨笛,表面钙化层如岁月凝结的琥珀,缝隙间沉淀着千年前的沙尘。“这物件在等省文物局的专家来清理呢。”她忽然笑了,眼角皱纹里落进星光,“女儿说清理完要对照敦煌壁画里的乐器图,说不定能还原出《摩诃兜勒》的曲谱。”
东方泛白时,我们蹲在考古队的塑料棚里喝砖茶。王秀兰用冻红的手指在平板电脑上标注塌方点,屏幕蓝光映着她别在鬓角的银发卡——那是枚北魏忍冬纹铜簪残件改制的。“父亲修文物用鱼鳔胶,女儿用纳米材料,”她将热茶浇在昨夜塌方的坐标点,“我嘛,就是块活着的夯土层。”
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时,锁阳城开始褪去鬼魅。王秀兰站在唐代城墙遗址上,背后是考古队新架设的全站仪。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与城墙裂隙里渗出的戍卒炭痕叠在一起。我突然看清她军棉袄肘部补丁的针脚——用敦煌壁画修复专用的蚕丝线,缝成了锁子甲纹样。
“今晚会有十七个摄像头盯着这片塌方区,”她弯腰系紧沾满碱土的胶靴,“但巡夜还得靠人眼。”靴面上凝结的盐霜泛着冷光,像撒了把碎瓷片。
走出工作站时,我踢到个锈蚀的铁皮盒。王秀兰说那是八十年代气象站遗物,现在装着女儿寄来的湿度传感器。盒盖内侧用红漆写着两行字,上一行是她父亲笔迹:“宁可碎骨,不叫文物蒙尘”;下一行贴着女儿打印的标签:“让数据开口说话”。
风又起了。那只汉代骨笛躺在我的采访本上,孔洞里钻出几粒新发的骆驼刺种子。

作者简介:诸纪红,男,1970年生,江苏南京人,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,江苏省散文学会会员,作品以乡土情怀为基实,记录社会发展、民情风采、乡村故事,见证时代变迁,文学、摄影作品散见于《光明日报》《农民日报》《香港文汇报》《江西日报》《黑龙江日报》《中国电力报》《老年知音》《老年博览》《晚晴》《绿叶》等报刊。
来源:转自《瓜州风》微信公众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