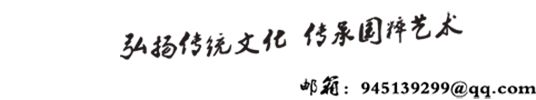河柳湾,顾名思义,就是因为在河道边有大片的柳树林而得名。每当夕阳西下,晚霞将柳树林染成金色,大人们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与羊群踏起的尘土混在一起,我们这些孩子总爱趴在桥栏上,数着归家的羊群,等待炊烟升起的方向。

记忆中,河柳湾的变迁总与土地的脉搏共振。最早记得的是“高高的山上种胡麻,胡麻地里藏娃娃”的童谣,后来胡麻地变成了麦浪,麦浪又化作代状田。直到那个背着帆布包的公社干部来宣讲“粮经比”,棉铃便在河柳湾的土地上绽开了白色的云朵。
拾棉花的记忆总与晨星相伴。天还未亮,灶膛里的火光就在母亲脸上跳动,父亲数着麻袋的嘀咕声穿过薄雾。我们蜷缩在毛驴车上,随着颠簸继续未完的梦,车辙在露水打湿的土路上画出蜿蜒的线。从春日的定苗到秋日的采摘,“脱裤腿”时棉株散发出的青涩气息,打尖时指尖沾染的汁液,都成了记忆里最鲜活的印记。故而,记忆中棉花种植一直是非常辛苦的劳作,每年的“五一”、国庆等节日,对我们来说是名符其实的在劳动和欢庆劳动中度过。

新时代的河柳湾,油门一踩便到了。老柳树佝偻着腰身,树皮皱得像祖父的手背。新修的机耕道笔直地刺向远方,那些藏在棉铃里的笑声、沾着晨露的吆喝,都随着磷肥桥的“远逝”而沉入了记忆的河床。只有风过柳梢时,还能依稀听见往日的回声…… (文/观点)
作者:甘肃敦煌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