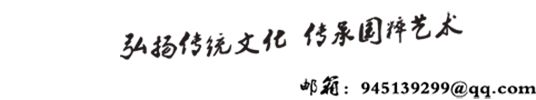学校不大,承载着窦家墩村远远近近六个村组的学生,大约也就一百来人吧。记得当时的学校也很简陋,一进校门的地方是一个大坡,走进校门,我们可以张开双臂,像小鸟一样飞向各自的教室。大坡左右两边是树林,种着白杨树、杏树、果树等,很大、很茂盛的一片树林。这里也是我们的劳动基地,时不时的,学校就会组织我们挖树、栽树啥的。可惜我的动手能力比较差,劳动表现总是乏善可陈,所以至今还记得。
那时候,我们最喜欢的是——比赛谁到校最早。真是,“干啥啥不行,到校第一名”。每天天一亮,简单地洗把脸,我们就将书包一拎,一路小跑,蹿到学校里去了。我们家在三组,距离学校算是比较近的,所以这个比赛,我们也总是比其他组的孩子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少不了会洋洋得意一下下。
冬天的早晨,伸手不见五指,漆黑一团,我和哥哥相约要早到校。当我们一溜烟地跑到学校门口,校门没有开,黑乎乎的,校门口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路,这时候都没有什么人,寂静又冷清,稍微有个响动也让人感觉又恐惧又刺激。我和哥哥拿出了火柴,将带着的蜡烛点燃照亮,“哧——”火柴燃起来了,映照出哥哥冻得发红的脸。
两人疑惑着,来得这么早,怎么度过这漫长的开校门前的时光?很快的,无聊就将我们的兴奋和愉悦感冲淡了。
这时候,随着一声门响,一个破锣般的女声从校园深处传来,声音又尖锐又高亢:“谁家的勺娃子这么早就跑上上学来了?闲的没事干了是不是?”骂声渐渐地向校门口这边逼近了。
是她,那个看校门的古家老婆子,我和哥哥吓得一哆嗦,赶紧吹熄了蜡烛,藏到了学校旁边的树沟里。
只听见那女声不依不饶,絮絮叨叨地骂了好久,一连串的脏话在校园上空盘旋了好久。慢慢地,慢慢地,才低了下去。听得出,那老婆子转身进了屋子。我和哥哥才松了口气,悄悄地从树沟里钻了出来。
我们终于当了一回“到校第一名”的喜悦感,很快就被这无聊和这古家老婆子的一连串吼骂给扫兴得光光的了。
记忆中,这位姓古的老婆子大约六十来岁,但她显得比我身边那些和她年龄相仿的老年人苍老得多。她又干又瘦,身材干瘪佝偻,穿的也很破旧,是一片灰褐色的衣服。她和她的丈夫负责看守我们的学校。与她相比,她的丈夫就沉默得多了,很少出声,学生经常能听见的,就是老婆子破锣般嘈杂的、尖刻的骂人的声音。
那个年头,看守学校大约是没有多少报酬的,就算有,估计也是微乎其微的。大约只有一个好处,就是可以不用和儿子媳妇住在一起,谁过谁的生活吧。
校长给老两口安排了一间比较大的房子,就在老师们办公室的旁边。我们上课、老师们办公的时候,很少见他们出来,偶尔见他们在校园里浇浇水、锄锄草什么的。古家的老汉瘦小而萎缩,在我们的记忆中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印象。
那个时候,我们都是非常天真,也很善良的孩子,老师在课堂上讲要“学雷锋”、“助人为乐”,还讲到“五保户”的时候,我们胸中就会鼓荡起熊熊的激情,就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,为我们身边的人做点什么。做什么呢?我脑子里突然就跳出了古家老婆子的形象。
我觉得,她是我见过的人里面,最可怜的了,穿的总是那么破旧,晦暗的一片,不像我身边的那些老奶奶们,虽然也很老迈,但总体上看起来是饱满圆润的。
我决定要帮助她。虽然我也不知道要帮她做什么。我想啊想,想起有一次老师让我去看门人的房子里取学校钥匙,那老婆子的房子里好脏好旧啊,桌子上、柜子上都是厚厚一层尘土,还是那种陈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尘土,显得他们的房子特别暗。要不,我们就去帮她打扫卫生吧。说不定卫生打扫干净了,古家老婆子高兴了,心情好了,就不会骂人了呢。
我向几个好朋友说了自己的想法,她们都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于是,我们寻了一个合适的时机——大约是其他同学都在自由活动的时间吧,我们来到了看门人的房子里,敲开了门,是我,自告奋勇地告诉那位老婆子:我们想帮助她打扫一下房子里的卫生。
说来也奇怪,平日里见了学生就讨厌,就开骂的老婆子,今天确实很高兴。她拉开门,让我们进去打扫,还嘱咐着:好好干,做干净点。
我们欣然入内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入这神秘的古家老婆子的房间,发现房间还挺大,里面的桌椅、灶台看上去都很陈旧,落了一层经年累月的、厚厚的污垢,那些污垢像是长在上面了似的。
我们几个立马开始干,扫地的扫地,擦桌子的擦桌子,我记得我帮助他们擦拭了桌子、窗台,甚至还有墙上挂着的一幅年画——胖娃娃抱鲤鱼,那年画上一层厚厚的、经年累月积攒的尘土,擦了好久,才勉强让那个胖娃娃变白了一些……
干完活要走的时候,古家老婆子一反常态,没有往日那样暴戾,还一遍遍地夸我们是好孩子。我们喜滋滋地离开了,胸中鼓胀着做了好事,似乎这个世界即将因为我们变得更美好的激情和快乐,走路的步伐也变得像小燕子一样轻盈。
后来,我们又去了几次,直到那个古家的老奶奶(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称她为“奶奶”了,因为她对我们变得友善了许多)把我们几个都认下了,把我们称为“几个好丫头”。
那时候,每个教室门口都有一块花坛,由这个班级的学生种植。我们种上了自己喜欢的花,八瓣梅、地雷花、千层牡丹等,大家一有空就爬在花坛边瞅啊瞅的,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种的花草破土而出,长叶子、开花。
老师的办公室门前是一大片长方形的花坛,校长把这个花坛安排给了古家老婆子和她的老汉一起种。
四月份,当每个教室门口的花坛都葱茏一片的时候,我们很惊奇地发现,老师办公室门口的花坛里长着一种奇怪的、没有见过的花儿。它的叶片有很多不规则的锯齿,像青菜似的。可它的植株上,却有明显的糙毛。分枝多,很纤细,叶片也很稀薄,感觉非常的纤弱。
五月份,每个教室门口的花坛都陆续有花朵开始开花了。老师办公室门口的花也抽出了一只只笔挺的花茎,结出了一个个卵形的花苞,上面也是毛茸茸的绿毛。
终于有一天,这些花开放了,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美丽的花儿:有红的、白的、黄的,一朵朵花薄如蝉翼,光洁如稠,将这片花坛变得光彩照人。风来时,这些花轻轻摇摆,似一群美人在翩翩起舞,风过了,它们静静伫立着,似一群美女在俯首自怜。花坛里似乎有一朵朵红霞在飘舞,又似一团团火焰在燃烧。
我喜欢这种花,几乎每天,每一节课下了,我都要跑到老师办公室门口一趟,偷偷地看这些花。这些似乎带着灵魂的花,妩媚无比,又娇柔自怜的花朵。我被这种花深深地迷住了。看看这朵,美得妖娆,看看那朵,楚楚动人。我尽情地看着,脑海里浮想联翩……
有一天,当我又一次沉浸在这花的世界中,忍不住凑近了,想闻闻这些花的味道时,突然,一个熟悉的、破锣般的女声炸雷似的从身后响起:“要不要脸?想偷花?你这狗娘养的……”随后,一连串脏话从那张嘴里喷涌而出,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下来了。
我吓了一跳,从花坛边一个弹跳,心狂跳不止。转身一看,正是那个古家老婆子。她一手叉腰,一手指着我的鼻子,将所有能想到的恶毒、肮脏的词语全部搜罗出来骂了起来,一连串响亮而聒噪的骂声在我的头顶荡漾,我想解释一下我没有偷花的意思,可她根本不听,一股脑儿地将积蓄已久的脏话全部“喷射”了出来。
那一刻,我羞愧难当,面红耳赤,但更多的,是一种复杂的情感。我想,她大约是认识我的吧,因为我已经几次到她的家里“学雷锋”去了,不是她一次次说我们是“好丫头”嘛,怎么今天,一翻脸就不认人了呢?
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。我虽然没有出生在一个“书香家庭”,但家里人是很少说脏话的。可今天,这个老婆子不但将我骂了,还连带着将我的父母、祖宗八代都跟着一起骂了,我被伤到了。
后来,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花坛看花,因为我知道那个老婆子死死地看护着她的花,冷不丁会从哪里跳出来,劈头盖脸一顿臭骂。
我们也再没有去过她屋里“学雷锋”。我第一次,对人性的复杂有了认识。
后来,在很多地方见到过这种花,看到这种娇柔得如同美女的花朵,看着它薄如蝉翼的花瓣像一朵朵红霞飘浮在花坛中,看着它在风中摇曳,时而叹息自怜,时而迎风起舞。偶尔的,童年时的一幕会重新浮现在脑海中,我会想起那年夏天我在我们的乡下小学里看到的那片美丽的花海,还有那个面容苍老、身材佝偻,满嘴脏话、语言恶毒的老婆子。
这种惊世骇俗的、奇美的花,叫做“虞美人”。

作者简介:窦艳丽:甘肃敦煌人,酒泉市作家协会会员,多篇散文作品先后发表于《北方作家》《甘肃日报》《甘肃农民报》《甘肃人口报》等报刊杂志和“阳关文学”等公众号。
组稿编辑/麻守仕 值班编辑/秋实